中山大學教授王致遠 四肢截肢後重新站上講臺

王致遠(中)四肢截肢後,仍重回校園教書,與學生關係融洽。
「為什麼不在家休息?」這是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王致遠重返校園後,學生在課堂問卷中對他提出的疑問。但對王致遠來說,教學不只是工作,而是他重新定義人生的方式。
當談到人生最沉重的轉折時,這位2025年師鐸獎得主,多次用了「玩」這個字形容。王致遠11年前因不明感染導致四肢截肢,但一年後他就裝上義肢,站上講臺上講課。他說,截肢把他做為一個人的基本條件拿掉了;但他又覺得,應該可以把義肢運用到某個很成功的程度,搞不好是另一種開始,「好像會很好玩的樣子!」
誤打誤撞開始教書,內心其實很恐懼
聊起為什麼想要當老師,王致遠笑說,是因為「誤打誤撞」跑去國外唸博士,回臺後發現商科博士學位在臺灣教職需求較高,就這樣當了大學教授。
王致遠說,剛開始教書時,他對學生其實很「恐懼」。他解釋,在國外念書時只要專注研究就好,但當教授要面對學生,讓他很不適應,甚至為了怕學生追著他問問題,他總是下課後就趕快逃離現場。
但教了一、兩年後,王致遠的想法慢慢轉變。當看到學生拿出紙筆,認真把他的話一句一句記下來、甚至下課留下來問問題,他才發現還是有學生會把上課當成重要的事,也開始反思自己的求學經驗,如何讓學生不要重蹈「上課很無聊」的覆轍。
開始逐漸適應教書後,2015年夏天的登山之旅,徹底改變了王致遠的人生軌跡。王說,那天夏天他和女友去爬山,回家後身體卻開始不適。前幾次就醫都被診斷為感冒,直到症狀嚴重到醫生警告「你生命跡象薄弱,趕快轉診到大醫院」,事態才開始嚴重。

王致遠(右前)會在開課時說明課程目標,清楚告訴學生這不是「涼課」。
一場怪病失去四肢,把復健當成探索遊戲
王致遠說,一開始他還想說「大概吊個點滴就沒事了吧!」沒想到沒多久狀況急轉直下。他開始呼吸困難、昏迷,肺部積水變白,接著敗血性休克,引發多重器官衰竭。為了保住他的命,醫院施用升壓劑,導致四肢缺血壞死,醫生告訴他必須截肢。
儘管之後王致遠將病歷送往各醫院評估,曾有醫師表示有可能復原,但最終發現情況相當嚴重,只有截肢一途。手術前,媽媽問他:「能否接受完全不一樣的人生?」他沒有回答,「我覺得這是唯一的選擇,沒有什麼好講的。」
截肢後,王致遠裝上義肢復健,重新適應自己的雙腳與雙手。他把復健過程當成探索遊戲,面對跌倒毫不畏懼。他笑說,反正多摔幾次就會了,而且出門也一樣會摔,「練習摔完之後要怎麼爬起來也很重要。」這種好奇心驅使他不斷實驗,「我會好奇沒手沒腳摔跤怎麼摔?好奇義肢手摔壞了會怎樣?現在我全都知道了。」
從裝上義肢到會走路,花了一個月;從開始練習控制電子手到滑手機玩寶可夢,則花了半年。他至今仍在玩寶可夢,笑說「老人比較死忠!」。
重返社會後,王致遠經常遭遇異樣眼光,但他選擇坦然面對。他從不穿長褲掩飾義肢,理由很實際——別人看到他的不一樣,就會理解他可能動作比較慢,可能需要座位等狀況。但同時也會招致不友善的歧視眼光,有人在麵店大聲建議他「可以用腳來吃飯」;有小朋友在高鐵站大喊:「阿嬤你看,那個人手腳都斷掉了好可憐喔」;更誇張的是在醫院,有人出於好奇心,竟然刻意伸腳要絆倒他。
面對這些惡意行為,王致遠解讀是「對這些人來說,他們也只是好奇吧?」他並沒有生氣,反而認為這是正常現象,只是苦笑:「他們為什麼會想要這樣做?」
回到校園,特殊經歷反而成為人生教材
回到校園後,王致遠也繼續精進他的教學。他認為學生大多是「不會問問題的生物」,開始設計各種吸引注意力的方式,如每15到18分鐘就安排互動活動等。他還發展出「篩選學生」的策略,在課綱明確標示:「這不是涼課,這課很操,想打混的學生就不要來!」
王致遠解釋,每個學生習慣的學習模式不一樣,與其花費很多心力處理預期落差,不如先設定清楚的課程內容,清楚分眾。這樣真正想從他身上學到東西的學生就會報名,也不會耽誤其他學生的時間。
因王致遠的特殊經歷,他也常成為學生尋求人生建議的對象,特別是面臨生死關頭的學生。王致遠說,自己並沒有接受任何專業的心理諮商訓練,所以他不會給建議,但他會分享自己的生命經驗。至於這個經驗有什麼意義、該怎麼做?他會選擇讓學生自己想。王致遠說,他很討厭說教,「只有你自己聽完、自己覺得有一些啟發的時候,這個啟發才是真的。」
2017年,王致遠完成臺灣首例雙手異體移植手術。他笑說,這就像武俠小說中的情節「欲練神功必先自宮」,移植雙手代表著他先前義肢復健得全部重來,還要長期服用抗排斥藥物,但為了追求獨立生活,他願意冒險一試。
王致遠說,別人可能會用「樂觀」來形容他,但他並不覺得自己「樂觀」,只是直覺認為「該怎麼解決這個問題」。這種看似輕鬆、實則堅韌的生命態度,或許就是他想要傳達給學生的人生教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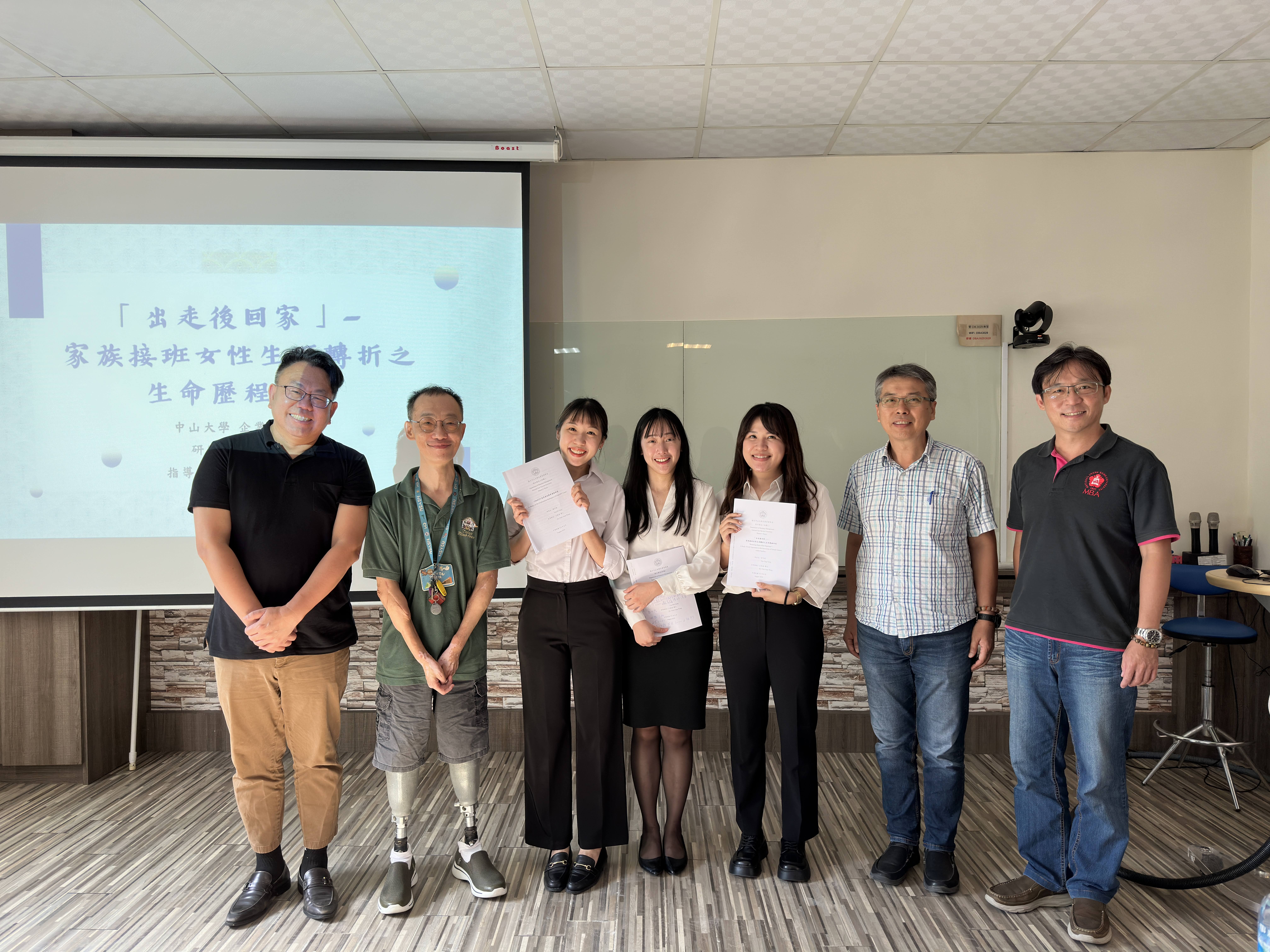
重返校園站上講台後,王致遠(左二)熱於指導學生,不論是課業或是人生方向。